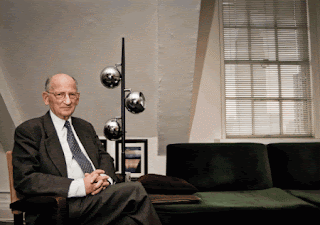※ 我可以在聽你說話的時候偷溜出去一下嗎?--- 談談中立化
督導學生跟自己做諮商最大的區別,就是不用親上火線。
除了實際在場之外,更有一種情緒上的清明(雖然有時候移情還是會透過受督者傳遞過來)。我想會這樣是因為督導不僅不在現場,心理上也跟病人保持微妙的距離。
這個特殊的位置對於中立來說非常重要。
相對的在親自治療個案時,會有當局者迷的情況。往往是在會談結束,反覆咀嚼的過程,心中都會興起一股"早知道"的扼腕!!
其實我們不用對這個"早知道,就..."愧疚,也不用在督導或個案研討的時候對於別人的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太過在意。
因為如果我們換成他們的位置,要想出這些,常常會是容易許多。
然而引我興趣的是:這個"早知道"都是發生在散步、運動、看書、逛街、甚至上大號等胡思亂想的時候。
簡言之,也就是輕鬆自在的時刻讓我們更容易去想。
這個領悟引領我思考工作時能否在心中保留一塊可以輕鬆自在的領地,特別那些容易讓人深陷其中的個案,他們往往堅持不懈地挑戰我們,在高張力下逼迫我們去認同他們在無意識的投射。
舉個例子,倘使案主說的東西讓我們昏昏欲睡,或許我們可以在心底偷溜出去散個步,翱翔在私密的無垠藍天,再從天空鳥瞰陷入這場僵局的我與他。
不,或許在這樣的對談中只有他,沒有我。因為我感覺不到任何參與而以昏沉抵抗。又或者,在這場對談中也沒有他;個案看似在說話、感受、思考,或許他所做的也只是盡其所能地遠離自己。
或許只有在這時候我們才會福至心靈,撥開昏睡的迷霧進而想到一點什麼。
佛洛依德在論述治療中立時提到,治療師在聆聽病人說話時,需要與病人的本我、自我、超我、與外在現實維持等距(同等的關注)。
這樣聆聽的好處是,可以持平均勻地聆聽,不會因為專注特定細節而失去大局。另一方面,治療師也才能不受病人內在動力的影響,跟病人的無意識玩起"帕博洛夫"的遊戲。
(阿智:這樣戲謔的比喻主要是為了說明,治療師因為受到病人無意識的引誘,成為病人實驗的白老鼠;當病人按下某個按鈕,我們就呈現特定行為,跟病人共同演出enactment。)
另一種無意識的引誘跟"滿足病人"有關。
病人總是要我們回答一些天經地義的問題,譬如:"關於我的問題請你告訴我怎麼做"?或者,"你覺得我這樣說對不對?"
標準的作法是保持沉默,避開病人設下的陷阱,不讓他們偷偷把心中分裂的兩端投射到我們身上。
保持沉默另一個好處是,可以退一步,感受一下,當下被問的時候,病人內在真正想表達的是甚麼?
沉默為病人還有我們拉出一片空間,讓我們可以從共同演出的舞台退下,身處觀眾席感受跟思考,為演出的戲碼感動,並且追尋屬於我們心中的意義。
※圖片是秘密花園諮商所一角,阿智攝影。
治療note16 :思想怠惰
很快地做移情詮釋,或許一種思想上的怠惰。
案主有談自己的需求,除了關注內在心智,還有案主與我們的關係;
我們也應該關注案主的現實生活,以及案主跟別人的關係。
不然我們會變得很像那種緊緊黏著案主的恐怖情人,不讓案主與我們在情感上分離。
※ 圖片選自網路
同志文化的角力
在同志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兩股力量彼此競逐
一股力量深以體制外的價值與生活方式為傲
一股力量則努力想融入主流社會。
(如:毀家棄婚派對主流陽光同志的批判)
這兩股對立的力量總讓我想到青春期的反叛
但因為同志長久以來不被接納的創傷而激化
如同一個青春期的少年,向父母吶喊著:
"少在哪邊告訴我要怎麼過生活!!你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
隨著多元性別平權社會的逐步到來,同志得以獲得更多支持
這個青春期的小孩才有機會可以擁有資源,逐步發展、成熟
也才有機會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去落實自己的價值與理念。
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應該可以讓每個人都擁有機會去探索
因此,這股敢於不同的聲音可以被看見,被欣賞
進一步形成批判體制與社會變革的力量,也會讓我們對價值
※ 圖片攝影阿智
治療note 15 :健康的自戀
健康的自戀就是可以真心喜歡自己,對世界有基本的安全感與信心。
然後又能深刻地了解自己,整合自己的向陽與陰暗。
沒有經歷過depressive position,涵容自戀的受挫,儘靠著過多的誇大與全能,很難培養出健康的自戀。
健康的自戀不是孤芳自賞,而是可以認肯別人的存在,知道世界不是圍繞著自己打轉。
因此,健康的自戀是一種流動的狀態,可以分享的能量交換。
※圖片選自網路
治療note 14:賦予意義
在臨床第一現場,傾聽案主的聲音
就會發現人生真的是一連串無意義的過程。
我們接收來自內外的刺激,應接不暇。
健康的人格會試著賦予這些雜訊統整的意義
讓自由意志可以為自己開出一條路;
不健康的人格則是被淹沒在這些雜訊中
永遠無法解讀出這些訊息的意義
只讓自己依循著過去的地圖盲目繞行。
(攝影: 阿智)
治療note.13 :並非無腦的純真
邁向年老的治療大師:歐文亞隆
與歐文亞隆以往極具分量的哲學三部曲《當尼采哭泣》、《叔本華的眼淚》、《斯賓諾莎問題》相較,
《一日浮生》呈現出十多段治療關係裡,殘存可貴的片羽,顯得像喧囂閉幕最後一道掌聲。
年老疾病、親密關係、自我追尋,在烏雲密布的生命終曲,如何呼喚和煦的片刻?透徹如光的見解能否穿透這些情緒波動?難道在死亡面前,都只能選擇和解?
歐文亞隆穿越治療方法的各種可能,直抵最根本的臨在,與對方全然地活在當下;
在不確定的陰雨下,望見逐漸不孤單的你,也看到越來越自在的歐文亞隆。
(撰文:小羊,編輯:阿智)
※ Yalom's Cure (亞隆的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q4Xte9H6FM
※ 圖片選自網路
#歐文亞隆 #Yalom #一日浮生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七 #性,攻擊與驅力
#精神分析味
市面上有些人聲稱從事分析取向的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更多人以精神分析詞彙來”分析”文學與電影。
但這些藉由案例故事或者華麗詞藻推砌的文本看來總是少了點甚麼?
細究應該就是少了精神分析味。
甚麼是精神分析味?
我想應該就是透過內省與神入的觀察方法所建立的無意識形構,在觀察的歷程中,可以把自己貼近觀察對象,浸淫其中又能進行分析思考。
讓我想起自己年初書寫宮崎駿的電影”風起”,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侘寂與生死本能理論,但怎麼上天下地的自由聯想,總感覺無法觸及自己開頭的提問:
“為什麼這部聲稱宮崎駿最後一部長篇動畫的電影,在我看完之後有揮之不去的釋然與傷懷?”
如果真有本領可以靠近這種無法言喻的感覺,
應該就握有精神分析的神髓吧?
《給孩子的夢想飛行器:宮崎駿與精神分析》
作者: 單瑜, 王明智,蔡昇諭, 林怡青, 彭奇章, 唐守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3567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七
#性,#攻擊與驅力
精神分析所講的性特質引起諸多困惑與爭議。
精神分析看待性經驗既不完全被經驗的內容所界定,也不是被身體的區域(性源帶)所定義。青少年看醫學插圖或許是種性經驗;但對醫學生來說卻一點也不性感。我們無法透過特定的生化物質(如荷爾蒙),對性特質的心理概念加以定義。心理學家卻能從生化研究中取得線索。
舉個例子:假使懷孕荷爾蒙與癌症相關,我們的心理探查就轉向癌症前期的性格?並且提問:這些人是否擁有慢性不孕的渴望? 既使如此,這種渴望存在的最終(心理)證據,還是要交給內省與神入來發現。
類似的考量當然也適用於生化學家從深度心理學取得的線索。
分析師雖然沒有大聲疾呼:性經驗的定義無遠弗屆;卻認為我們所想的性遠比生殖的性更加遼闊。
前生殖期的性(經驗)包括:性的思考歷程、性的動作、還有與之相關的事物。
單單玩味弗洛伊德在“性不雅”這檔事(10)嚴肅兼玩笑的註解就很有意思 。他戲謔地加註:“總括來說,我們似乎並不完全了解,當一個人此用"性"這個詞的時候,到底意味著什麼(10)?”
因此,兒童前生殖期的性(經驗),與成人的性/經驗(無論是前戲,倒錯,抑或性交)共同擁有一個無法被(進一步)界定的性質,就是眾所周知”這就是性”的東西。不管是經由直接的經驗,抑或是透過長期的內省,移除了(內省的)障礙(阻抗分析)之後。
或許可以這樣說,對於嬰兒與兒童,許多經驗具有成人性生活最熟悉的性質;我們的性生活(阿智:應該是指成人性生活)為我們提供了比早期心理發展更加廣泛的經驗殘餘。
佛洛伊德曾想選用這個詞彙“potiori ”(11),意即在所有經驗中最被知曉的; 換句話說,這個字無可爭議地招喚出存於我們自身最對味的意涵。
如果這個詞(的涵義)屬於生物學的話,那麼不見得一定要堅持使用”性”這個詞。7
不只對性特質,諸多內省經驗的連續體(continuum) ,如:攻擊與敵意,也可如此細究。
弗洛伊德拒絕放棄它(阿智:使用性這個詞),視其為維護心理(意義)本質的唯一途徑。若是換成"生命力"與"心理能量"等詞,就無法帶給我們那種”曾被拒絕的原始經驗(模式)”切中要害的理解。
假使我們認為精神分析的“驅力”同樣來自(內在經驗的)內省,事情將會清楚許多。如果這些經驗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驅力(想要,願望或奮力)的特質,那麼驅力就是無數內在經驗的抽象表現;意味著無法透過內省進一步分析的心理特質;也是性與攻擊的最大公約數(共同點)。
弗洛伊德對於原始自戀與受虐的假設,奠基於內省心理學的理論架構。他觀察了自戀和受虐的臨床事實,假設它們是早期性與攻擊(潛在)經驗(理論)復甦的形式,以後來的形式(臨床上的自戀與受虐)復返來回應環境壓力。
與原始自戀與受虐平行的生死本能假設,則造就全然不同的理論建構。愛神與死神(的概念)不屬於內省與神入觀察方法的心理學理論,而是屬於不同觀察方法的生物學理論。
生物學家當然可以自由地採納任何心理學的有用線索; 然而,他的理論還是必須基於生物學的觀察與證據(17)。其他如,對生命體(to all animate matter)內省心理學方法的應用,譬如在某種形式的目的論生物學中8,就不再是科學。
因此,儘管我們欣賞弗洛伊德生物學的大膽推測,我們仍須了解,愛神與死神(的概念)不在分析心理學的架構之中。
因此,無法藉由(精神分析)內省觀察的發現加以確認,弗洛伊德通常會拒絕生物學的推測。
----------
8 Ferenczi的Thalassa(3)(阿智:指的是海洋,意指汪洋感?)是內省和神入過度擴張的絕佳範例。
類似的實證科學例子記載於他對女性性特質的論文中。
有許多討論認為弗洛伊德具有憎女偏見,因為他強調陽具欽羨(phallic strivings)對女性性特質發展的重要性。
明顯的生物學事實似乎是,女性擁有原初的女性傾向,因此女性特質不能被解釋為從令人失望的男性特質中撤退。佛洛伊德被其盲點所侷限,減輕了觀察力道,並不那麼令人訝異。
他拒絕改變對女性性特質的看法,更有可能是因為依賴臨床證據---特別當證據透過分析觀察向他敞開---因此他拒絕接受一個似是而非的生物學視框做為心理學事實。
在接受生物學的雙性特質之後,佛洛伊德洞悉了病人的女性態度與感受,總是發現其中具有對於陽具欽羨的掙扎(the struggle over phallic strivings) 。在沒有心理證據的情況下,他否定了先前的女性氣質心理階段假設。
弗洛伊德對女性性特質發展的態度,不過就是忠於內省與神入觀察方法眾多例子之一。
更重要的是,儘管他對分析觀察的忠誠普遍偏高,仍傾向於懸置自己的概念,並將其置放在生物學與心理學之間的無人之地。一旦開始執行(操作),這樣的邊緣地帶就不復存在。
從這個角度來看,驅力如荷爾蒙等生化物質(即操作定義的生物學)的動力觀點,並不會比把超我當成解剖學的結構觀點會為更妥適。
(阿智:會有這個結論是因為透過內省與觀察的分析心理學,在操作上看來,當然比生物學假設與觀察,對於人類的內在世界來說,更合理也更實用。)
#阿智翻譯於:Heinz Kohut, M.D.的”Introspection, 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六
因為口頭禪有其起源學,聽者往往會有突兀之感(如我)。然就像嬰兒尋找母親的乳房,也許為了生存,也許為了在這變換多端如履薄冰的象徵界,得以稍稍喘息。
我們當然知道形成這個假設不會比性器、肛門與口腔情慾經驗(内省)的發現更早,也無法比移情所喚起的伊底帕斯激情更早。
然而,再多想一點會發現,不是所有假設所使用的概念,在未經修改的情况下,都能被看做是透過内省與神入的觀察所得。
倚賴的概念也能從這點加以思考,稍後我們再討論驅力與性特質的問題。
第一個含意指的是兩個有機體(生物學)之間的關係;亦或兩個社會單位(社會學)之間的關係。生物觀察者可以肯定新生的哺乳動物倚賴該物種母職(成人)所提供的照顧(為了生存)。同樣關於倚賴的判準也適用於兩個(人類)成人間的關係。
在我們複雜且高度專業化的文明中,社會成員只發展出某些技能,因此為了存在,得倚賴整個社會(他人的技術總和),更可能也是為了生物的存活。
然而,倚賴這個詞除了生物學或社會學的意義之外,心理學(概念)也沿用同樣的名稱,在精神動力概念的形成中被廣泛運用。
當我們談到口腔依賴型人格,並得出結論地認為,口腔依賴可能造成他們希望可以延續跟分析師的關係(阿智:或者永遠無法結束關係)。
當我們在此處理精神分析的依賴(概念),必須假設我們是透過分析來觀察(我們的)病人,才得到這些概念,(阿智:倚賴)這個術語是由被分析者精神狀態(的整體與抽象)所組成。
事實再明顯不過,比方當我們說一個病人正掙扎於依賴與否時,換成另一種結構性的概念來說(阿智:科赫特在此使用結構性,指的應該是精神的無意識結構),他已潛抑了它們(阿智:指這些衝突)。
退行作為精神分析術語,意味著回歸至早期心理狀態。因此,我們的問題不在於嬰兒依賴母親(生物或社會學意義上)這樣無可爭議的事實。令人費解的是,當我們揭露成年被分析者潛抑的倚賴掙扎時,他的精神狀態是否與我們發現的事物大致相關?
當然,心理學家時而從生物學(發現或原理)中尋找線索,使其對觀察事物有所依循。假使從生物學原理推斷的具體心智狀態的解釋是錯的,尤其與心理發現相矛盾時;最後的判准應該還是回到心理觀察本身。
成年人對依賴的執著,要是退化至童年狀態,就不是回返到正常的口腔發展階段,而是那些通常發生在童年後期的兒童病理。
它們是對明確拒絕(經驗)的反應,既暴怒且害怕被報復的複雜混合體。或藉著緊緊抓住治療師(在此成為病人全能地投射自戀幻想之良性載體)來保護病人自己(如:對抗與隱藏的結構性衝突相關的罪咎或焦慮之浮現)。
然而,不受生物期望所束縛的同理觀察,對各色各樣的驅力仍保持開放的態度,特別讓自己(治療師)處於一種接近未完的狀態(不完全的精神分析式禁慾---何時將會完成?)有助於治療師創造一種Hörigkeit(束縛)的狀態。
因此,這是一種對於緊緊抓住的執著,而不是與(使心理狀態懸置的)特定驅力產生關聯。或許(能被想到來解釋這些狀態)最普遍的心理原則就是抗拒改變(“力比多的粘著性”the adhesiveness of libido);但也只有在窮盡其他可能之後,或在特殊條件下對此因素有直接的(心理)證據時,才能考慮這個(最)普遍的解釋。
他是集中營三十名倖存者之一,在多年被拘禁的過程中,約有十萬人遇害。當俄羅斯步步逼近,納粹自衛隊放棄了營地,三十名囚犯因此重獲自由。儘管他們身體狀況良好,仍將近四天無法離開營地。
譬如一些成癮者,沒有(取得)安撫自己或睡覺的能力;他們沒能將早期的安撫經驗轉化成內在的能力(結構)。因此,這些上癮者不得不依賴物質(或俗稱的毒品)作為客體關係的替代物,而不是心理結構的替代物。
倘使這些病人正在接受心理治療,可能會被說成對治療師或治療程序上癮。但是他們的上癮不能與移情混淆:治療師不是既存心理結構投射的屏幕,而是它的代替物。
此刻,由於心理結構是必要的,病人真的需要治療師支持與舒緩。他的依賴不能被分析,或者藉由頓悟而減少,而是需要被看見與被認肯。病人首先得學習把因著社交孤立造成的無意識自大,轉換成對於倚賴現實的痛苦接受。
娛樂性用藥與自我認同的無限迴圈
hiv使這種情況更為艱難,更強大的污名,把帕斯提男同志推入更深的躲藏,更強的自我厭斥中。
當這股被用力壓制的情緒匯聚成陰影,只會使我們更加恐懼,更加孤獨。
終至無路可退...。
透過藥物,我們一方面可以不讓自己感受到這種無以名之的巨大痛苦;另一方面,因為隱藏所帶來的孤獨,亦可以透過藥物的體驗稍加舒緩。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渴望愛。
"找到自己,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http://www.lourdes.tw/
https://www.terra.com.br/noticias/ciencia/pesquisa/festas-que-misturam-drogas-e-sexo-preocupam-especialistas,8a81059654046410VgnVCM3000009af154d0RCRD.html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五
如果錯把因為分析治療而生的人際關係誤認為真實的人際關係(譬如個案希望可以跟治療師做朋友),恐怕是一種情感上的錯置。
然而,真正的愛情又不免沾染移情的影子(我們幾乎都是透過愛情來再現昔日與父母的關係)。
所以孰真孰假終究也是真假難辨,柯赫特簡單的文字道盡一切:
這些觀點沒有考慮到分析觀察的基本組成本來就是內省的。因此,我們必須將人際關係這個詞(在分析中)定義為:朝向內省的自我觀察而敞開的人際經驗;它與社會心理學家及其他人使用的人際關係詞彙,如互動、交易等...截然不同。
持續內省導致移情精神官能症,認出某種發生於內在(嬰兒特質和反作用力之間)的鬥爭。分析師相當程度作為移情人物,並非在人際關係的框架中被經驗,而是作為被分析者無意識內在結構的載體。
譬如:一名病人若無其事地報告說,他在分析途中逃掉了公車費的支付。他“注意到”分析師在幫他開門時臉色異常嚴肅。分析師作為移情人物(帶著抗拒不斷內省)成為被分析者無意識超我力量的表達(無意識父親意象)。
對精神病兩大(早期)發現是:弗洛伊德對精神病性慮病(8)的理解,以及陶斯克(Tausk)的對同理或內省的認知。
精神分裂症被機器控制的妄想乃早期自體形式的復甦(而這些經驗在與“你”接觸後旋即失落),退行到痛苦焦慮的身體經驗中。(21)。持續反思自戀型疾患與邊緣狀態,使我們認識到無結構的心智如何奮力與古老客體保持聯繫,抑或保持著微妙的分離。6
5. 關於記憶軌跡的接受作為一種結構概念,參見Glover(14)。
6. 在精神病和邊緣狀態中,與邊際客體(marginal object)鬥爭的內省經驗和人際關係的觀察截然不同。研究這兩種理論統合的結果頗具啟發性,可以透過諸如"參與觀察者"之類橋接概念的使用來達成。在這種觀點中,精神官能症的移情客體之結構概念與自戀疾患的古老人際客體之間的豐饒區別已蕩然無存。結果就是出現邏輯和內在一致的精神病理學概念,多樣的臨床現象反而被視為精神分裂症的變異或等級(20)。
------------------------------------------------
分析師在古老的人際關係框架中藉由內省經驗到,他是被分析者試圖聯繫的舊客體,並由此經驗中分離出自己的認同,或者從中蘊生內在結構的一小部分。
例如: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漠然退縮的狀態下抵達分析會談。在前一天的夢中,他身處積雪覆蓋的荒涼地; 一位女人提供給他乳房,但他發現乳房是橡膠製的。病人情感的漠然與夢乃對於明顯一分鐘的反應,而非在現實上分析師對病人的拒絕。
在精神病和邊緣狀態的分析中,古老的人際衝突佔據(策略的)核心;與之對應的乃是精神病精神官能症(psychoneuroses )的結構性衝突。在細節上,同樣的考量也適用於精神病會遇到的結構性衝突 。
弗洛伊德關於移情的基本定義(5)乃明確概念形成的結果:移情是無意識試圖跨越既存潛抑屏障(雖然經常被削弱的)時所產生的影響。被分析者對分析師的覺知所產生的夢、症狀、與觀點,均是移情浮現的重要形式。
目前移情反移情術語的混淆使用(常是社會心理學(意義)的具體人際關係),源自理論框架必須在建立操作模式下所產生(毫無覺察)的不一致。如果我們將早期移情概念融入1923年(12)的結構學,額外將其定義為關於自我的自主權(16);就能保持操作一致的優點,而不受弗洛伊德於1900年粗糙的心智模式所束縛。
它會清楚劃分成兩種經驗:(1)努力朝向客體,雖從深處浮現,卻不會越過潛抑屏障(參考弗洛伊德“自我和本我”:源自本我的潛抑屏障只會分離出一小部分的自我),和(2)源自自我對客體的努力,原屬於移情,後來與被潛抑的部分斷開,成為自我的自主客體選擇。
重點是要去認出在這兩種情況下,客體的選擇部分源自過去,其後的客體選擇則被童年的模塑所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移情都是重複的,卻不是所有的重複都是移情。
後者能透過持續內省加以解決; 前者則居於結構衝突的場域之外,並不直接受分析內省所影響。
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
生命故事團體成員備忘錄
說故事的人
1. 針對你想探討的生命主題,準備一系列的小故事,可以是現實人生的際遇,可以是夢或幻想。避免僅僅說一些抽象形上的感覺、概念或想法。
2. 說故事時想像自己是故事的編劇、導演或說書人,把故事說的「立體」很重要,注意故事中要有人物、場景、情節、聲光畫面。當然你也可以運用任何你喜歡的輔助工具來讓故事說得精采。(照片、錄影帶、音樂、娃娃。)
3. 說故事時讓自己完全投入其中,說到有感覺很重要。建議可以使用「現在進行式」來說,更能帶出豐富的感覺。
4. 可以為每一個小故事取標題,說完所有的故事也可以為它取標題。標題可以是故事的地標,取一個有創意的標題往往也代表你對故事獨特的看法。
5.放掉理性與邏輯: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天馬行空、隨意錯置都可以,在故事的安排與敘說上讓你的創意奔馳,你一定可以找到屬於你獨特說故事的方式!
6.真心誠意:你可以決定自己在團體裡要說多少,但注意一定要真心的說故事。
聽故事的人
1. 基本態度:放鬆自己,把自己完全放空(意味著把所學的概念與理論忘掉),把自己投入裡面(就像投入電腦的虛擬世界中)。這是一種美的欣賞歷程(如同看一場好的電影),而不是專家想要解決問題、或者給建議的歷程。
2. 有感覺很重要,帶著情感去聽。
3. 細細品味每一個小細節:劇情、人物、顏色、味道、感官、思想、情感、行為等等。讓聽故事聽起來很「濕」。如果說者遺露了小細節(說得很「乾」),藉由問問題協助他說(你可以問的問題有「人」、「事」、「時」、「地」、「物」、「感覺」等等…。)。
4. 故事拼圖:每一個小故事都像是一個未完成的小拼圖,試著去串連它們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你可以去看這些故事的「高」與「低」,也可以去體會故事的「輕」與「重」、更可以細心留意故事反覆出現的「主題」,體會故事所蘊含的「力量」,看它們如何在故事的發展中展現它們獨特的樣子!
5. 標題:可以為每一個小故事取標題,聽完所有的故事也可以為它取標題。
6. 相信:相信人的生命是美麗的、有意義的。縱使面對故事的「苦」、故事的「惡」、也願意在聽故事的過程中努力去追求故事的「善」、與「美」。
7. 浸淫在無意義中的能力:所以也要有種能耐,去忍受在還未挖掘出意義時的延懸狀態。
8. 分享與回饋:試著把你的體會說出來,與說故事的人交換意見。他的故事所激盪出的你的故事,也可以是很好的分享。
(阿智寫於:2003,09,02)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四
#試穿別人的鞋子
#而不是把你變成他
閱讀這篇論文,忽然對於IPA會長Stefano Bolognini來台演講同理心的某些段落了然於心。
他曾提到認同與同理心的不同。認同就是你變成他,換句話來說就是失去你自己;而同理心僅是試穿別人的鞋子,你可以體會到個案穿鞋的感受,又不會失去你自己。
這與科赫特不斷強調的,同理心(神入)作為深入個案內心世界的觀察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在同理別人時,並不會被淹沒在個案主觀的情感與世界中,而是可以把這些徐徐如生的體會當成某種觀察的對象,持續思考。
以科赫特的話來說:
“分析師透過內省和同理來區辨,既不是有效無效,也不是複雜簡單,而是憑藉著內省的自我觀察者與其同理對象保持一定的相對距離來達成任務。”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四
#早期心智組織
(阿智:科赫特在這個段落中持續思考:內省與神入的方法如何針對早期心智組織提出觀察?要保持怎樣的姿態有利於觀察?
行文間為我們釐清這是形式與內容的問題。
科赫特毋寧認為有必要區辨,內省與神入的形式/方法論,與客體關係理論所揭露的內容,是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向度。
把握住形式,有利於進行有效的同理。)
我們不僅要面對反對內省的非理性阻抗,也要面對現實的侷限。譬如,針對作者論述的(或理論)擬人化,成人化等批評。以現有的語彙來說,這些批評認為觀察者的同理過程未盡審慎; 或作者的提問被錯誤同理。毫無疑問的事實是,當被觀察者與觀察者有愈多的不相似,同理的可靠性也隨之下降。
精神分析始於起源學,將人類經驗視為各種複雜、不同成熟度等心智組織之縱深的連續體。因此,在心理發展早期階段,倘若我們要同理自己、以及同理自己過去的精神組織非常不容易。(這些方法上的考量當然不僅適用於縱深面,也適用於橫向面,譬如當我們談到心理深度和睡眠期間的心理退行,神經症,疲勞,壓力等...)。
當我們描述原始、早期、或深度的心理過程時,怎樣的概念可以為我們所用?舉例如佛洛伊德實際精神官能症(actual neuroses)的症狀中,持續的內省(以自由聯想和阻抗分析的形式)也無法揭露任何焦慮精神官能症,或神經衰弱之疲勞與疼痛(4)以外的心理內容。弗洛伊德偶爾遇見的那些變化多端的幻想,相當確定是建立在這些症狀的續發(就像合理化作用)作用上。
缺乏心理上的發現使得弗洛伊德認為實際精神官能症(actual neuroses)就是一種干擾有機體的直接表達,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開展了更多非內省的調查方法。譬如,3弗洛伊德將神經干擾對照於心理干擾,幾乎意味著藉由生化方法來進行心理精神官能症症狀的檢查(6)。類似的考慮也適用於以下心理病理:神經干擾,3植物型精神官能症(1)或器官型精神官能症(2),並用來區分心智發展的早期(功能)階段(15)。
我們同樣不該假裝對心智發展最早階段的心理內容有確切的了解,而應該在討論這些早期階段時,避免提及爾後經驗類似現象的術語。我們必須滿足於寬鬆的同理近似值,以張力取代願望,以張力下降取代願望實現,以凝縮與妥協取代問題解決。
(阿智: 簡言之,就是不要用發展晚期的語彙,來形容早期的現象。)
討論早期心理狀態,比起用錯術語更困難的是操作的轉換;不是將同理內省的退化形式擴展到早期心智狀態,而是對社會處境的描繪,譬如描述母親與孩子的關係。研究和描述母子早期互動當然不可或缺; 但不要忘記我們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轉向一種需要比對、且不等於內省心理學的參考架構。
因此我們務必小心,不要將立基於觀察的理論(透過內省的幫助),與立基於觀察方法的理論(比方說社會心理學者或生物學家使用的那種)彼此混淆。
水流下坡,避開石塊,尋覓奔赴河流之最短路徑; 為的是解決水與其環境的適應問題。一個已婚婦女,陷入不忠誘惑的衝突之中,遂發展出歇斯底里的失明 - 再次地解決了適應問題。另一個女人在類似的情況下決定不再被誘惑; 也不想再看到引誘者,急急忙忙地趕回家,從而解決了適應問題。
社會心理學家試著比較各種複雜性,用來區分這些適應歷程;生物學家則是試著比較各種解決問題方法的複雜性--不像我們這個時代在電腦的視框下僅做出簡單區辨。
無論社會心理學家或生物學家如何解決問題,顯然與精神分析師截然不同。
分析師透過內省和同情來區辨,既不是有效無效,也不是複雜簡單,而是憑藉著內省的自我觀察者與其同理對象保持一定的相對距離來達成任務。一些心理過程(新生兒的緊張,與張力的釋放)幾乎超出了同理與適應的範疇,其所發生的適應毋寧更接近於水與石頭、重力相互作用所產生的運動。
其他過程雖然比上述種種更靠近同理的觀察者,仍離觀察的自我有段距離:譬如我們稱之為原初歷程的(以精神官能症的概念來說):妥協形成,凝縮,置換,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 );還有我們最終認為更接近內省與神入心理歷程的:邏輯思考的次級歷程,問題解決,深思熟慮下的行動;種種決定與選擇的能力。(待續)
#阿智翻譯於:Heinz Kohut, M.D.的”Introspection, 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
#圖片選自日本攝影師,森山大道的作品。曾於其自傳作品《犬的記憶》中自稱流浪狗,「在路上像排泄似地在街頭各處拍攝照片」
https://repnathandowning.wordpress.com/2015/03/04/daido-moriyama/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三
在每次治療開始的時候,總會伴隨長長的沉默
有時候長的,連我都會忘記時間流逝
就後來剩下的時間看來,或許我幾乎用掉一半的時間來保持沉默。
當然不是。
沉默的時候我於內在進行某種狂野的自由聯想
只是這些想像以某種畫外音的方式進行,自行發展衍伸
因為太過狂野,獨自面對都覺得害怕(dread),更別說把它們說出口。
而且還是向另一個人說(通常是治療師,生命中的他者)。
也讓我對於後來增加次數的案主於治療開始時長長的沉默,
保持包容與開放。
我知道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我與他們一起來到無意識的水潭
總是猶豫著,是否涉水而過?
似乎有一種因著精神分析方法而產生的阻抗,以高度理性化(阿智:合理化?)來表達自己:這是一種對內省的阻抗。
我們似乎羞於直接提及它; 而且從未提及—既使伴隨許多缺點 – 內省打開通往偉大發現的路徑。
拋開對內省顯得猶豫的社會文化因素(例如“神秘”,“瑜伽”,“東方”,“非西方”等流行語),依然潛藏某種偏見,抗拒去承認觀察方法可以使我們收穫良多。
我們習慣藉由行動不斷地排空,只有當思考可以作為行動的中介,作為延遲行動,測試行動,或者計畫行動時;我們才願意接受思考。
內省似乎與我們當下希望可以釋放張力的種種作為相抗衡,加上對於被動、還有對於潛抑內容當下被揭露所帶來的張力,及隨之而來的恐懼。
誠然,精神分析的自由聯想在這層意義上與我們一般思維(過程)並不相符。
一般來說,思考是“一種實驗性的行動,伴隨著相對少量宣洩的置換”(7)。精神分析治療可說是對行動(自由)的準備;然而,自由聯想本身並不為行動而準備,而是通過對於漸增張力的容忍度,來進行結構的重組。
就分析師這端也會感到類似的不適,阻止我們在分析方法的實驗中去探索因著內省時間的加長所帶來的結果,如:延長分析時間所帶來的(治療)效果。
更多的是,在自我(ego)對內省的控制下仍被快樂原則所影響,如神秘邪教和偽科學的神秘心理學,乃是內省的合理化形式(rationalized forms )。
然而,對內省的濫用不能減少其作為科學工具的價值。畢竟,非內省的物理科學追求,在科學家使用科學來滿足其病態目的,可能等同於被未經修飾的快樂原則利用。
然而,精神分析的內省並非被動地逃離現實,最好是積極,追尋,與進取的。作為最好的物理科學(阿智:應該是指精神分析),相當程度被欲望所驅動,去深化和擴展我們的知識領域。(待續)
https://instarix.com/media/BUqHlUll_ZP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二
#內省與神入作為心理學的基本組成
看著這些齜牙裂嘴的抗議人士,扭曲著臉哭喊著,才發現這一刻要動用同理心可謂困難之至,不過還好這時候自己已經下班了。
若要同理這股酸楚,心中浮現是另一股夢想成真的不真實感受,當你這輩子沒有把結婚放在生命的選項,並且動用所有的防衛去處理這種失落(不管是親密關係上的,或者是被主流社會拒斥的),頃刻間形勢逆轉,你忽然不知道如何面對原先建立起來的巨大防衛。
一個人丟下一塊石頭,墜落的石頭殺死另一個人。 如果存在可以神入的意識或無意識意圖,那我們說的就是心理行動; 如果沒有這樣的意圖,我們會認為這是物理事件的因果關係。另一方面,如果以物理和生化的詞彙加以描述,由A說話所發出的某些字詞聲波,如何在B的大腦啟動某種電化模式,這種描述也沒有包括:B被A激怒的心理事實。
因此,以明確的描述來重複之前的定義:如果我們的觀察模式包括內省和神入作為基本組成,我們就將這些現象稱之為心智,精神或心理的。文中的“基本”一詞表示(a)內省或神入無法自外於心理觀察的事實,以及(b)神入也能單獨存在。
我們首先必須考慮可能的反對意見:即精神分析觀察的主要工具並非內省,而是藉由分析師對病人行為(自由聯想)進行審查。然而,以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為例;透過自我分析發現大量臨床事實,並從這些事實發展抽象理論。
對一般的分析情境,以分析師作見證人的角度看來,精神分析就是對被分析者內省式的自我觀察。事實上,分析師的心理洞察力往往超越被分析者對自己的理解。然而,這些心理洞察卻是受訓良好的內省技巧作用下的結果,分析師將內省(代理內省)延伸,使用這些稱之為神入的技巧。
就這點看來,在科學心理學之外使用同理(阿智:神入;之後會將兩者交替使用)十分常見。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態度並不系統科學,總是傾向於將現象多少看成心理或心智的,這多少也取決於我們對觀察對象的同理能力。
對動物也是一樣:當一隻狗在分離之後迎向牠的主人,我們知道在我們與狗的經驗中,還有狗與親愛的“你”於分離結束後所經歷的一切,總有一些共同的部分。於是我們開始以心理學的方式來思考,即使我們會強調人與動物的經驗差異甚巨。然而,幾乎沒有人會說這是植物心理學。
然而,由於我們並不承認植物具有基本的自我意識(就像我們也會對動物這樣做),所以這樣的形容更多具有寓言或詩歌的意義。更誇張的,如果我們觀察下山的水流尋覓最短的路線以避免障礙,仍會以擬人化的語言來描述這些事實(疾馳,尋求,規避等); 但不會有人會說這是無生物的心理學 - 甚至比說這是植物心理學的人來得更少。2.
https://www.facebook.com/twreporter/photos/a.1646706185577247.1073741828.1646675415580324/1907397829508080/?type=3&theater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一
#精神分析的同理心(神入)
日前IPA的會長來台演講,題目就是精神分析中的同理心。
除了談到同理心這個概念的複雜與運作之不易之外(幾乎有點盡人事聽天命了)
還使用了遼望遠山的比喻,在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將山峰美景一覽無遺
當天氣不好的時候,在怎麼用力看也看不出所以然。
這個比喻讓我想起科赫特把同理心(我更喜歡稱之為神入)當成觀察內心的工具
彷彿磨練這項能力,就獲致深入內心城府的基本配備似的。
這項比喻讓人感覺新鮮,也對同理心這項工具不過於理想化,只求隨時保養精煉而已。
《內省,神入,與精神分析---在觀察與理論模式中的關係檢驗》 #之一
這是1958年1月24日所提交的版本。
這篇論文首先於1957年11月,芝加哥所舉辦的芝加哥精神分析學會二十五週年會議上發表。之前於1957年7月,巴黎舉辦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大會上已介紹簡短版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和動物在知覺器官的幫助下探索(investigate)周遭環境; 他們聽,聞,看,摸; 形成對周圍環境的統一印象, 記憶這些印象,比較它們,並根據過去印象來預期未來。 這些探索變得越來越系統一致, 知覺器官透過儀器(望遠鏡,顯微鏡)可以增進其功能, 觀察到的事實經由概念化的思考橋接(本身無法被觀察),整合至更大的單位(理論), 藉著細膩的步驟,逐漸發展出探索外在世界的科學。
然而上述的區別是對的嗎? 思想,願望,感覺和幻想真的沒有物理性的存在嗎? 有沒有一種潛在的過程,一方面可以透過高度精細的物理方法來記錄,另一方面仍可被體驗為思想,感覺,幻想或願望?這個古老又熟悉的問題只要以心身二元(或聯合)的(替代)形式提問,就註定無解。 唯一有用的操作型定義就是, 當我們觀察的(基本)要素包括我們的感官時,我們說的就是物理現象,當我們觀察的(基本)要素為內省和神入時,我們說的就是心理現象。
當然,上述定義無法被狹隘地理解為特定時間所發生的實際行動,而是觀察者對被觀察現象廣泛的整體態度。那些無法直接觀察的行星仍會影響行星的運行,然而天文學家還是可以思索那些尚未出現在望遠鏡裡的天體運行,大小,與(亮度)等級; 他們持續思索那些歷經數年仍無法回返卻可觀測到的慧星(物理性質)。
類似的考量也可適用於心理領域。舉例來說,在精神分析中,我們認為“前意識”和“無意識”是心理結構,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帶著內省的意圖來接近它們,也不僅因為我們透過內省最終可以抵達它們,還因為我們是在內省或潛在內省經驗的架構中來考量它們。
隨著我們組織觀察資料,我們的觀察變得科學與系統化,然後我們開始處理與觀測事實距離稍遠的各種概念。這些概念中的某些部分由抽象與概括組成,或多或少仍直接與觀察現象相關。
以動物學的“哺乳動物”的概念來說,主要來自各種不同動物的具體觀察; 然而,哺乳動物本身卻無法被觀察到。心理學也一樣。 例如:精神分析中的驅力概念(稍後我們會詳述)來自無以數計的內省經驗 ; 然而,驅力本身不能被觀察到。其他概念,如物理學中的加速或者精神分析中的潛抑,並不直接等於觀察現象。無論如何,這樣的概念清楚地歸屬於不同科學的總體框架,因為它們為觀察的數據描繪出之間的關係。我們觀察空間中的物體,記錄其沿時間軸的物理位置,從而獲得速度的概念。我們從內部觀察思想與幻想,觀察它們的消失與升起,從而獲致潛抑的概念。
但是,內省與神入真的是心理觀察的基本組成嗎? 我們可以透過外部世界的非內省式觀察來確認心理事實嗎?
讓我們設想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到一個異常高的人。 毫無疑問地這個人的異常身高是我們的心理評估的重要事實 – 然而,沒有內省和神入,他的身高僅是一種物理屬性。
只有當我們站在他的立場,只有當我們透過替代的內省,開始感受到他的異常身高就像是我們自己的一樣,我們內在經驗才可以生氣勃勃,沉浸其中,彷彿我們如此醒目或異常,只有我們開始待在那裡,珍視異常身高帶給這人可能的意義,我們才能觀察到心理事實。(待續)
#阿智翻譯於:Heinz Kohut, M.D.的”Introspection, 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八
#靈光乍現的時刻
生命中總有一些時刻連舒伯特也無言以對,閱讀好的論文也是這種心情。
肯伯格從嚴肅的議題出發,有層次地發展論述,在實務上細膩敏銳,也在理論上擲地有聲。
寫到後來幾乎是一種情懷了,可以看到他對精神分析的情感與相信,這種相信接近於信仰。
用信仰形容並非是褻瀆,而是說明那種由內心深處傳達出來的關懷,如此具有力量。
也是因為這種情感的力量,甚至甘於被個案怨恨與誤解,堅持不懈地做有用的事情。
也讓後輩的我們甘於堅守在珍貴的第三者位置。
#第三者的後設心理學
相形之下,整個分析體驗必須對當下互為主體進行分析時,就像在冒險將無意識衝突轉譯成更具現實基礎、此時此刻的經驗;亦可終止抗拒深化無意識理解的防衛。防衛性地固著(fixation )在互為主體溝通的(相關)表面,會強化那些"對抗更深層次的多型性倒錯嬰兒衝突(polymorphous, perverse infantile conflicts)、原始施虐受虐、以及將衝突普遍性慾化"的防衛。
事實上,分析師以"第三者"反思病人在主體間發動的無意識衝突,活化了伊底帕斯移情;也說明了發生於病人與分析師的所有互動,無法規避移情的影響,當然移情也無法完全被解決。
不應該把詮釋當成整個(病人與分析師)關係的指示,好像關係僅由無限退化的移情所組成。倘使如此最終會否認關係的現實,並導致(阿智:病人的)嬰兒化。真實的關係在某一點上沾染移情的色彩,構成了昇華的殘餘,也是日常生活客體關係的尋常面向之一部分。
Laplanche(1987)的原慾色情化之原初誘導理論( theory of the original induction of libidinal erotization)提到:母嬰關係中藉著母親"神秘的"訊息,使嬰兒在無法了解這些訊息的情況下被經驗到(阿智:母親的誘惑?)。
分析師的無意識始終存在並影響病人,並不是說可以對分析師在前意識中預想、在意識中成形的詮釋假設予以打折。這些均促成了病人容忍與分析師分離,接受最終無法全然了解分析師這個人,並且也認知到分析關係如何複制代間的分離。
這些考量強調擴展病人深度無意識探索的重要性,而不是將分析師的介入限制在互為主體的框架中。
後者傾向於強調相對於伊底帕斯的前伊底帕斯關係,相對於古老伊底帕斯與生殖期性特質的前伊底帕斯的本能發展。
唯有當分析師被經驗為"分離"的個體時,這些(阿智:不同)才有機會出現並被探索。同樣的,病人和分析師在整個治療過程真實且逐漸演變的分離,使其對分析師以及分析師(從外在觀點)所建構的真實發展出昇華的好奇心。
我認為,持續地分析移情與修通所產生的結果為:病人與分析師“真正關係”的發展;此為治療進展階段非特殊促成的成長面向(a nonspecific growth-promoting aspect of the advanced stages of the treatment)。亦導致了部分的昇華性認同,在結案階段有助於修通憂鬱移情和哀悼反應。這個過程以分離與親密的能力達到高峰,因為差異與失落而滿懷感激。
在"彷彿"(模式)中形成詮釋,不僅連結到病人過去(特殊)特定的某一點,也等於認肯了移情活化之無意識衝突的同步性(synchronic nature )。也就是說,這不僅是在移情中活化的單一事件或創傷經驗,而是相關衝突與防衛的凝縮( condensation);來自諸多暫時、不同、遙遠、卻在認知上與無意識連結的經驗,這些早期經驗坐落在不同時期,再慢慢被分解成不同的組成。
簡言之,無意識衝突的歷史性質從固置於病人性格結構的歷史性凝縮( synchronic condensations )中演變而來。因此,在治療進展階段,病人會明顯退行到過去特定的片刻(specific episodes from the past),特定記憶的重現反映出某種轉變,將此刻的互為主體轉化成過去重要的無意識經驗之復返。
但如此的復返鮮少導向無縫接軌的歷史(an integrated, seamless history):事實上退行與進展幾乎同步,創傷(經驗)總是藉著回溯(retrospectively )娓娓道來,而非直接被經驗到。這也說明了發現過去的無意識與當下的關係具有不連續本質。
關於詮釋本質的最後定奪:"詮釋是導致事實的揭露?亦或導致創新的敘事(the creative generation of a new narrative)?"
我相信,最好的詮釋來自對病人主觀經驗、和那些不得不被潛抑(repressed)、解離(dissociated)或投射(projected)的種種,同理性的理解。
慢慢擴大(spreads out)“此時此刻”無意識意義的理解,為的是要闡明“彼時彼刻”無意識經驗。因此詮釋始於揭露此時此刻的意義,再慢慢連結到過去的意義;這個過去決定了現在經驗的本質。
分析師的創造力以各種方式去捕捉移情中整體的情緒氛圍,來形成詮釋。運用他對病人口語和非口語行為,及對自己反移情(反應)的觀察,分析師構築了一個足以捕捉此刻氛圍的隱喻,但也對此保持開放,不帶期待地允許病人依循自己的方向探索。
首先詮釋可以是暫時的陳述、提問、或者數種替代性方案,僅供參考;但最終應該會變得愈發犀利與聚焦。它們時而增加病人的痛苦與焦慮,時而會帶來解放,甚或令人振奮。
分析師對真實的追尋,無可避免地有時會被病人視為侵略:假使分析師對真實的追尋,基於真心希望病人可以增進對自己的理解。最終病人有能力可以諒解,並感激分析師堅定不移地站在真實的這一邊,反思著(阿智:病人的一切),使得病人可以在自己的力量中滿懷信心。
總結來說,我對精神分析理論和臨床實踐兩種當代取向廣泛進行比較:一種是我認為的精神分析主流,另一種則代表了人際-互為主體-自體心理學取向。
我提出的觀點是:藉由“第三者”分析的可能,使用它來探索普遍的無意識內在心理衝突,伊底帕斯與前伊底帕斯,以及隨之而來的精神病理。
而藉由停留在“兩人”分析的後者,往往將探索過度侷限在前伊底帕斯舞台,可能會限制在移情中探索無意識衝突的深度,及發展病人自主的自我反思功能。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七
#討厭的父親打破母嬰的完美融合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七
在臨床實務中,相信很多治療師都會有同樣的經驗。
明明是帶著善意的幫忙,或者是自認有洞察力的詮釋,卻被個案經驗成攻擊。比較嚴重的情況是,案主可能在躺椅上睡著了,而且每詮釋必睡無疑。
好一點的情況是,病人可以透過語言表達這種挫折與委屈:
“我感覺你沒有與我同在,我們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或者,”今天我覺得你把我打倒了,為什麼你如此不了解我?”
這些起初令人困惑,隨即發展成罪疚的場景,案主帶著足以淹沒治療師的謾罵與抗議,在在訴說著母嬰關係中完美融合被打破的創傷。
肯伯格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將詮釋帶來的反思功能視為打破兩人關係的父親角色,這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這個討厭的電燈泡,如何拿捏他的登場,著實是每個治療師需要再三琢磨的課題。
#第三者的現身促成病人的反思功能
Rainer Krause對精神分析與分析治療的情感溝通研究(Krause,1988; Krause和Lutoff,1988)有著重大的突破;為潛抑、解離、與分裂的情感經驗溝通,或者如何在無意識中登錄提供客觀的證據。語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證明了這個過程對於意識溝通的影響。Krause的研究結合了意識溝通的意義分析,與情感經驗的無意識溝通,以及對話與可觀察的情感溝通之外的那些溝通經驗的反思,讓我們更貼近互為主體的客觀研究。
前述的法國精神分析將分析師的功能化為"第三者"(third person)的概念。從外在角度來詮釋移情反移情的關係本質,象徵地複製了打破前伊底帕斯(母嬰象徵化關係)的伊底帕斯父親(角色),由此孕生而出古老的伊底帕斯三角。
帶有精神官能性人格組織的病人具備這樣的功能,有能力把自己分裂成行動與觀察部分,代表了三角結構的確切建立。分析師能對反移情進行自我反思的探索,也反映了這個三角(阿智:的建立)。
然而,對於邊緣型人格組織的病人,分析師的詮釋(角色)會被經驗為某種對於病人與分析師共生連結(symbiotic link )的暴力性打斷。也正好就是這樣才能頑強地抵抗所有創傷的衝擊:發現父母的伴侶關係、世代與性的不同、對父母關係的妒羨、原初場景的震驚…,種種最原始層級的挫折與焦慮以一種恐懼被滅絕的形式和此三角建立息息相關。
在此,比昂(1968)對於(阿智:病人)藉著偽善、傲慢與好奇的鐵三角,防衛地破壞在認知上獲得洞察(insight),乃是(阿智:病人)對早期三角覺察無法容忍所致。
在各種情況下治療嚴重退化的病人,重要的動力往往是,病人會把詮釋經驗成當他們死命尋求與分析師融合時的猛然打斷。這可能會限制(病人)情緒的成長與發展,使其表現低於原本可達到的水準。
分析師作為第三者(as a third person)的功能是反思的重要來源,最終會成為病人的自我反思,為內省、洞察、與自主(introspection, insight, and autonomy)的發展帶來強大刺激,其中包括自主地尋求對更深層無意識動力的進一步了解。
我認為在治療進展階段的最佳狀態下,主導移情/反移情發展的「互為主體之活化」,藉著內化分析師的反思功能,將逐漸讓位給主導病人(他或她)主觀經驗溝通。這顯示出病人有能力去反思主觀的經驗,當自我發現超越了當下互為主體經驗的考察,更深層的無意識於焉浮現。
退行與移情的深化,以及病人原始經驗的關係進展,都將在自我可以容忍原始幻想威脅時發生。就這點看來,病人更能容忍分析師的分離與獨立,在分析探索中也可以把分析師視為滿懷關心卻截然不同的參與者,既使如此也能感到安心。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 圖片為把自己戳瞎的伊底帕斯,象徵不希望看到真相,或者不想啟動反思功能的病人。選自網路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六
#如何不讓互為主體變成治療師與病人難分難解的投射場域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六
互為主體的理念在後現代解構思潮的影響下算是近幾十年的顯學,對心理治療的影響不一而足。
常見的現象常發生在齊頭式的平等:譬如心理師的自我坦露增加了,或者大膽如Yalom不忌諱對女病人表達”性”趣。或者治療界線逐漸滑坡,導致治療結構傾斜失衡,然後內在的衝動失去涵容的空間與可能。
這種在臨床上發生的案主與心理師過於投入彼此,導致投射失去可以涵容與思考的空間,終至難分難解的險境。
讓我們進一步思考:互為主體所珍視的主觀性(不管來自治療師或者病人),如果沒有分析工作的客觀性做基礎,可能會帶來的危險。恐怕也讓治療失去更大的效益:反思(reflection)的功能與可能。
因此肯伯格在這裡提出震耳饋聾的解方:三人心理學。以下這段不僅交代歷史淵源(Fenichel與Bion),並提出強而有力的提醒與批判。
#從兩人心理學到三人心理學
Richard Sterba認為(1934)將自我分裂成觀察部分與行動部分 ,代表自我反思功能的活化。主要來自對照顧者反思功能的內化—不僅是媽媽對寶寶自身經驗的神入。同樣的,病人不僅藉由分析師的神入來增強自我反思能力,也藉由(而且非常重要地)認同分析師第三立場的反思功能來達成。
簡言之,我認為我們需要三人心理學,而非一人或兩人心理學。此第三人乃"分析師作為與病人互為主體關係參照"的獨特角色來達成。
當然,分析師會有誤用或濫用其特定功能的危險:任意對待病人、威權主義、或者教化病人等非移情/反移情等態度都是。
毫無功能的權力所帶來的危險(濫用功能權威的危險),對任何行使權威的工作來說,都是一種根本的危險。但是藉著消除分析師在治療情境中現實與功能性的權威來保護病人對抗這些危險(阿智:的說法)也太過天真。
把分析師觀點與病人等同的平等意識形態,此種反移情與移情一樣病態(no more or less pathological),都是一種對分析情境的扭曲。(阿智:應該是指在權力位階上完全平等,典型的情境是病人會對分析師說,我跟你說了這麼多,但我對你一無所知,這讓我感覺不被尊重。或者為什麼你可以跟我請假,我卻無法跟你請假?)
最好的情況是,詮釋僅提供假設,再看看個案概念化會帶來什麼結果,好決定詮釋的適用性(阿智:原文 confirmed or disconfirmed)。它們會因隱喻的使用而增強,並且最好擁有不飽和的品質(“unsaturated” quality ),也就是說不要在特定理論假設下,與病人過去的歷史相連結。(阿智:不管是緊抱著理論,或者用力施加起源學詮釋,恐怕只會侷限思考)。
簡言之,它們聚焦於“此時此刻的無意識”,期望詮釋過程會逐漸深化並找到起源學的方向,只要病人與分析師可以遵循自由聯想並觀察移情/反移情的發展即可。
以上種種導致我想探究當前對詮釋客觀性的質疑,否認詮釋形成的標準具有客觀的性質,以及把建構主義偷渡到唯我的相對主義中(the potential slippage of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into a solipsistic relativism)。這裡所指的詮釋標準之最初設定,相關的論述有自我心理學的 Otto Fenichel (1941) 以及克萊恩學派的Wilfred Bion (1968, 1970)。
Fenichel的詮釋後設心理學研究建議詮釋要有三大守則:經濟學的(本能釋放的領域),動力的(由淺入深,從動機性防衛到衝動),還有結構的(從自我面開始詮釋)。如果我們用本能強度(特別是libidinal)取代他的經濟原則,那麼詮釋的指標將集中在一小時(阿智:應該是指單次的session)情感主導的內容。我相信我們會被帶往Fenichel一般性的詮釋原則,而這些原則支持詮釋的客觀性。
比昂同樣建議分析師對特定時間所發展的整體影響保持開放,不帶任何先驗理論去詮釋"選擇性事實"(selected fact)。或者依循分析師的衝動,往特定方向推動病人(“無憶無欲的詮釋”)。比昂用不同語言提到相似的架構,如何選擇材料如何進行詮釋,皆根據特定時間內病人與分析師關係之主要情感發展來決定。
不幸的是,比昂在生命最後幾年逐漸轉往神秘的方向,暗指分析師的"選擇性事實"發生在他(或她)直觀地捕捉心理現實,某種缺乏普遍基礎的感官現實。而今這種看法,與我們透過表面與其它能完美觀察的溝通管道所增加的情感溝通知識相矛盾。
比昂藉著描述病人無法涵容之無意識衝突透過投射認同帶給分析師的影響,開啟了一條通往反移情探索的道路。矛盾的是,他卻拒絕考量分析師對這些投射認同的情感反應,特別當它們以各種方式與分析師獨特的脆弱相連結時。
(阿智:這讓我想到一般來說我們對反移情的考量除了病人的投射之外,通常還會考量因分析師個人議題所產生的反移情;後者通常需要透過分析來解決。)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 圖片為提出分析治療的客觀性基準的Otto Fenichel,選自網路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五
#從限制中找到自由 #最好的分析學習從實際體驗開始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五
在督導學生的過程中,學生對於我怎麼”想”到這些事情(個案概念化與詮釋)充滿好奇。
這讓我想到自己學習的過程,除了理論閱讀與聽課之外,最大的收穫就是來自與治療師或督導互為主體的互動,臨在地為我示範這個維持架構與反思的姿態與功能。
這個寶貴的姿態就是肯伯格所說的”第三立場”,這個超然的位置,獨立於分析師與病人、主體與客體、移情與反移情。
它可以有多大的心理空間,多少的自由聯想,就可以使得分析擁有多大的自由,對於治療本身來說也可以有多大的可能。
弔詭的是,這些自由往往要從限制中奠定基礎。
這讓我想到侯孝賢早起受限於成本的拍片過程,無法請得起職業演員(或大明星),沒有昂貴的設置器材,因此只能起用非職業演員,然後儘量在自然的環境、固定的景框中去思考拍攝。
卻也因此造就了他獨特的電影美學。
而治療的限制就是治療架構,透過架構的建立,使得治療可以形塑基本的骨架。
在我看來,治療架構也像是一種邀請,分析師悉心維護,像是搭建一個互為主體的關係舞台,好為接下來的互動提供體驗、觀察與思考的空間。
#分析架構與第三立場
我認為精神分析包括三個“架構”(frame):
第一,治療架構或分析設定透過一些治療性的安排來產生。包括治療時間,地點,以及多久碰一次面,由病人與分析師各自遵循... 。這個架構透過真實人際關係的設定來建立,如Hans Loewald(1960)所定義的:一個需要幫助的人,相信另一個擁有知識經驗及良好意圖的人,兩者的相遇。此另一人(阿智:分析師)並非帶著全知全能給予幫助,而是對幫助病人懷著實際的興趣並試圖努力,同時意識到這一努力的局限性。
第二個架構的產生端賴分析師技巧上的中立,還有對於抗拒自由聯想的防衛、及抗拒移情退行的活化加以分析。分析架構允許病人內在客體關係重新活化(reactivation)與共同演出(enactment),還有與之相應的衝動/防衛配置;並且闡述互為主體這一區塊,使其成為分析探詢的對象。在分析架構營造的促成環境中(facilitating enviroment),移情反移情配置的共同演出很快就會扭曲治療架構的真實關係。
第三個架構是由分析師將自己內在分解成參與移情/反移情綁定的體驗部分與觀察部分(包括分析師的具體知識,技術工具和對患者昇華的情感投資)。這是詮釋過程必不可少的第三架構。其中包括了分析師讓自己沉浸在移情反移情關係裏,並透過詮釋功能保有自己得以抽身。這種分析師將自己從移情反移情裡抽身的反思姿態,並且詮釋這種被移情反移情退行所扭曲的治療框架的意義,構成了“第三立場”,此乃來自法國分析的用語(De Mijolla和De Mijolla Mellor,1996)。
我認為,第三立場是分析工作的重要前提。意味著分析師超越了移情/反移情處境,並提出新的視角,以澄清在移情中活化的無意識衝突。通過內射認同(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機制,幫助病人發展自我反思功能,好作為自我(ego)增進其處理內在衝突能力的一部分。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 圖片為拍片中的侯孝賢,選自網路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四
#我的互為主體治療反思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四
記得以前碩班所接受的人本主義訓練,讓自己練就一身認同案主的"本領"
當時所學的"互為主體",幾乎可說是齊頭式的平等,換言之就是抹平諮商師與案主之間的權力位階
並且以為,從權力不平等的思考出發,可以達成互為主體的實踐。
另一種互為主體的思考,則是讓諮商師變得透明,認為在雙方均透明的情況下,可以為案主賦權。
在這種思考下,自我坦露變得輕易許多,但這種輕易現在想想不禁捏把冷汗,
因為治療有可能一不小心,成為諮商師自戀的舞台。
後來轉向精神分析取向,才慢慢看到自己認同案主的背後,原來有自己所投射的種種
也才發現,過於認同案主,容易讓治療輕易變成單一敘事,也就是案主的敘事,或者是治療師與案主互相融合的敘事。
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治療師與案主難分難捨,治療性空間卻愈發侷促,也容易陷入僵局。
(當然,這種僵局對於目標或症狀導向的短期心理治療或許永遠也不會碰到)
因此細讀肯伯格這篇論文,談到治療師除了認同案主的主觀世界之外,還有一種珍貴的價值就是提供自己的主觀。
不僅是自己所感受到的主觀敘事,還包括自己與案主互動過程中如何貼近案主的主觀敘事。
簡言之,治療師不僅把觀看的結果呈現給案主,也把觀看的方式呈現給案主。
透過這個細密的過程,治療性空間由點到線到面,然後撐出三維甚或四維的空間。
而在治療中可以撐出這樣的空間,心靈才有自由,治療也才有機會找到出路。
※※※※※※※
#認肯寶寶的經驗很重要 #同時還要加上自己的
截至目前的摘要看來,我的取向與互為主體所注重的相互吻合。也就是在病人與分析師互為主體的經驗中去活化二元性的客體關係。
但我認為除了澄清病人主觀經驗的基本功之外,更要去詮釋那些病人可能沒意識到,或者不想意識到的事物。
病得愈嚴重的病人,實際上愈是透過行為來傳達重要訊息。因此,透過自由聯想與病人主觀經驗的脈絡,對這些行為委婉地予以面質、澄清、以及整合性的詮釋,正是澄清移情總體特性的一大重點(Kernberg,1993)。
這樣做時,分析師也以一個不同(阿智:於病人)的外在客體角度來澄清他(她)的經驗與觀察。
結合病人的主觀經驗、非語言行為、以及反移情所得出的訊息,並予以評估,給出了分析領域的全面觀點(global view of the analytic field)。
分析師的主觀經驗不是一種“特權”,病人的也不是:分析師對其詮釋保持開放,把它視為可修正的暫時性假設,亦可促使病人願意修正他(或她)對自己經驗的假設(阿智:原文以counterpart ,對應的部份來形容)。
分析師不僅澄清了互為主體的界域,並加上新的向度:“局外人”的觀點,反映病人和分析師所經驗的種種,並傳達出他對病人主觀經驗的理解。
上述那種普遍將分析師反映他與病人互動的任務加以放大((expansion)阿智:的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對背後所隱含的那種,透過移情與母嬰配對之鏡映過程的理想化加以批評。對後者來說,不同的意義皆被歸結於鏡映,從Kohut(1971)對嬰兒兒童經驗的理想化接納與認肯,到瑪格麗特·莫勒(Mahler,Pine和Bergman,1975年)聚焦於嬰兒經驗的現實反映,到拉崗(Lacan,1949)把鏡映視作自我異化的基本來源。
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去區分“認肯嬰兒的經驗",或者"向他傳達外在不同的客體正在對它認肯的經驗":
當一個母親對嬰兒交流(conmunication)"她能對孩子在她這邊經驗到的種種表達同理"時,就是在幫助它去組織或解構 - 它的情感經驗。
母親的同調包括她對寶寶的看法。 因此當她可以同理時,便向寶寶表達出她的理解,並且對此做出回應,其中包含反思的要素(an element of reflection) ,最後通過內化過程成為寶寶自我反思的功能。
當母親對寶寶的經驗同理失敗,卻試圖強加自己正在經驗的感覺在它身上,這不僅是同理失敗,對寶寶的經驗來說,更是侵入的行為,導致某種程度的內在分化(differentiation),某種被侵入的客體再現所淹沒的瀕危與潛在創傷的自我再現。
總之,母親肯定寶寶的看法,同時加上自己的,對於被妥善同理的寶寶,提供了自我反思的潛在面向。 導致如同Peter Fonagy(個人傳播)說的“心智化”。
透過類似的過程,分析師的詮釋活動認肯了病人的主觀經驗,拓展了病人對人際關係所激活之客體關係的覺察,並促進了外在客體(包含客體自己的主觀經驗)觀察功能的內化。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 圖片選自網路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三
#翻譯是很好的精讀
翻譯是一種精讀,也是一種反覆揣摩作者對文章的鋪陳及用意的最好方式。
雖然這種方式慢如蝸步,仍有其價值。
第三大段內容非常多,接下來要分好幾次刊出
Kernberg開始說明自己對於互為主體取向的批評
文章一開頭,開誠布公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並坦承立場會影響論點,自己的論點也是眾多看法中的一部分。
算是客客氣氣的開始,因為這麼客氣,讓人不禁對於之後的批評有如坐針氈之感。
前面主要是對於移情反移情在分析設置下如何運作有著精闢的看法
特別這種看法並沒有把本能理論與客體關係對立起來
(就我了解,許多客體關係的信徒,早把本能理論拋到九霄雲外)
而是連結這兩種典範,因此非常值得參考。
行文非常抽象,文字的密度也高,建議大家反覆琢磨,慢慢消化。
※※※※※※※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三
#來自當代主流觀點的批評
我對"自體心理學-互為主體-人際取向"簡要的批評如下。
因為清楚地意識到:不同來源的互為主體概念,本來就有非常不同的論點;
故我的評論自然無法對諸多微妙差異能有公允的看法。
我的背景自然會影響到我的論點(1993):其主要建立在佛洛伊德二元驅力的基礎上,致力於整合自我心理學與客體關係理論,並將它們與當代的情感理論相結合,我相信這個觀點大都被分析主流所接受。
總結這些立場,主要是為了對後續評論鋪路。
首先,我認為可分析的心理病理反映了無意識的內在衝突,這些衝突全被整合到病理化的內在結構中。這個結構由驅力與防衛功能所投注的內在客體關係組成。
在分析設置中,病人的任務便是要執行自我聯想,分析師的任務便是要在移情中診斷與詮釋被活化的無意識衝突,這構成了分析治療的基本元素。
把移情分析置放在分析工作的核心,並不代表忽略外在衝突。
在實務中,分析的核心總是聚焦於大量情感投注的材料,不管這些材料發生在移情或者發生於外在。
這些內化的客體關係將驅力的再現物固置(fixate)於某種形式中,充滿情感地連結到自體與客體的再現。自體/客體的二重性有著相當程度的(且相互的)矛盾與衝突,因此扭曲了心智裝置(psychic apparatus)。
換句話說,自體與客體(二重)的再現(單位)之情感配置,既是與驅力相關的衝突貯存庫,也是心智裝置三重結構的標準配備。
當無意識的內在心智衝突在移情配置的形式中重新活化,便顯露出原初的內在客體關係。
當代觀點將反移情看成分析師對病人所有情感的反映,捕捉病人對反移情的貢獻(特別透過投射認同,但不僅如此,還有透過全能控制的機制),以及分析師透過反移情對移情配置的潛在參與;特別在異常高張與退化的情況下運作的移情演出。
我認為反移情的分析(在反移情中分析師對病人一致及互補的認同)對於分析無意識衝突乃關鍵工具,
這些被活化的衝突主要透過反移情,情感地投注到內在客體關係的形式中。((我要特別說明:佛洛伊德作品中關於agieren的意義並非"行動化"(acting out)或者"共同演出" (enactment),更接近的說法是法文中的"通往行為的途徑"(passage a l'acte)。
對於移情反移情有效的分析只能發生在與分析設置相關,共同演出的關係脈絡中。))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二
讓我們繼續來爬梳精神分析中的互為主體趨勢
這篇論文第二大段一路讀下來
好像忽然可以明白這場發生在美國的精神分析革命
如何地挑戰精神分析界的古典金科玉律。
也了解十年前在台灣大紅大紫的Yalom,還有他的人際關係學派
原來都是互為主體潮流下的分支。
照片是Yalom跟他文學教授的太座下廚的場景
強調治療師平易近人的一面。
※※※※※※※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二
#互為主體與人際取向的發展
特別在美國,與“分析主流”發展的和解相平行的趨勢,一方面存在於自體心理學,另一方面則在當代人際分析所表現的文化分析傳統中。 這些發展在臨床與理論上摘述如下(Summers,1994)。
臨床上,自體心理學聚焦於"自體-自體客體"的移情,並將其視為分析治療的主要模式( as a major matrix of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這也意味著它離開了傳統與當代主流的技術中立。
後柯赫特學派的自體心理學,分析從提供自體客體功能的架構,轉成重視情緒同調乃治療的基本工具。藉著分析師的神入、主觀融入病人的經驗、以及認肯互為主體的現實,協助病人澄清自己的主體性。上述特性均建立在分析師與病人的主體性交會中(Basch,1985; Ornstein和Ornstein,1985)。分析師的"自體客體功能"藉著澄清病人的情感經驗,轉變成"整合的功能"。透過強調分析師對病人主觀經驗持續地同理與融入,心理病理的缺陷模式與衝突模式在此交會。這個取向還強調反分析師權威,質疑分析師特權,並質疑技術上的匿名與中立。(Stolorow,Brandchaft and Atwood,1988)。
另有一股略有不同但與此相關的趨勢,朝著同樣方向前進。側重分析師的補償角色(阿智:矯正性情緒經驗?);特別對於病人過往古老自體的過度刺激或刺激不足,以及雙親(角色)的缺席(或匱乏),導致後來自體發展的脆弱。 這種方法可能源自自體心理學,和母嬰關係模式,強調分離-個性化的缺乏與衝突。
這個取向的作者認為分析師相對於病人的主體性並無二致,分析師(與病人)經驗的相互澄清,可以豐富病人的情感,促進病人的人格成長。就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而言,Gill 與 Hoffmann (1982)側重分析師性格對移情的影響,以及移情與反移情之相互辯證與依存,可以作為分析探查的領域。
這種分析觀點全面轉換的結果是:質疑分析師客觀面對病人的傳統實證觀點(這些病人會帶著移情扭曲還有成長起源來接受分析),代之以建構模式;在分析情境中探索新的情感關係發展,將其視為相互理解的基礎;並且認為,病人對這種情感經驗的溶入乃主要的療效因子。
對於病人主體性特權的強調導致更進一步的結果,離開移情詮釋的攻擊觀點。假設攻擊乃病人與分析師正向關係的失敗,還有神入與同調的失落;因此我們應該做的是探索這些失落,更甚於把它詮釋為病人的內在衝突。
事實上,各種不同的技術取向來自不同的理論背景,卻在哲學上共同質疑分析師詮釋與一人心理學的客觀性(one-person psychology),質疑分析師保持客觀,以澄清病人內在生活的功能。這些取向也轉變為"詮釋的建構論",使之更切合敘事真實,而不是歷史真實的再建構,並以客體關係理論取代驅力理論。
事實上,某些作者會把自體心理學視為客體關係理論的一部分,注重關係模型(matrix)中促進成長的正向觀點,而非透過衝突所內射進來的負向客體關係。所有的客體關係與互為主體取向最終都指向母嬰關係,還有分離個體化所造成的創傷。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圖片選自網路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一
#互為主體與精神分析
這學期的報告我選"互為主體與精神分析"的單元
主要原因是念輔大研究所時,互為主體一直是老師念茲在茲的精神。
而精神分析的中立與匿名性,還有分析師的權威,怎樣都很難把它跟互為主體聯想在一起。
這篇論文的作者肯伯格是美國精神分析大師,主要貢獻在於將客體關係與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融合在一起。
看看博學的他如何思考互為主體的議題,應該可以學習很多。
※※※※※※※
《詮釋的內涵,互為主體與第三立場 》
#之一
Sidney和Esther Fine(1990)總結了四大精神分析觀點,重新確認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ical(他們稱之為“古典的”),科赫特學派,克萊恩學派以及肯伯格取向之間的差異,並詢問:“這些差異會造成甚麼不同?留待未來研究者回答。"
我打算透過自我心理學,英國學派和自己工作(阿智:肯伯格取向)的技術融合,平行對照科赫特學派和人際分析取向演變的融合,來探索一種逐漸發展的精神分析新趨勢,以朝向全面性互為主體的關係取向。接下來,我將比較當代精神分析兩大方向,並且對於不同取向如何影響詮釋,表達自己的立場。
#當代精神分析技巧的演變趨勢
直到十年前,聆聽英國分析學會的演講,仍然很容易區分當代弗洛伊德學派,克萊恩學派和獨立學派的觀點。 時至今日,這種區分變得越來越困難。 隨著自我心理學,獨立學派與克萊恩學派各個傳統的和解,分析技術的演變也應蘊而生,我認為在幾大方面得到進展(Kernberg,1993):
1.當代弗洛伊德或自我心理學取向,有一種明確的趨勢,更早且更系統地詮釋移情,在這方面,趨近於克萊恩技術的方向。
2.越來越強調把反移情的分析當作材料,以整合到移情詮釋裏。在此,自我心理學的技術趨近於英國學派的方向。
3.越來越強調角色分析,克萊恩學派趨近於自我心理學的方向,尤其是克萊恩對於“病理組織”的強調(Steiner,1987,1990),影響分析師對(病人)關係的詮釋,以及移情發展所產生的併發症(阿智:應該是指移情精神官能症)。
4.越來越強調對“此時此刻”的無意識涵義加以分析,以及“由淺入深”的詮釋,這把克萊恩學派的分析更帶往自我心理學的方向。
5.越來越關注精神分析情境中的(主要)情感,作為選擇詮釋材料的基礎,這使得自我心理學和克萊恩學派趨近於彼此的方向,且相互倚賴。
6.客體關係的理論模型對心理病理的理論技術愈來愈有影響力,三個支流最終在此匯聚成精神分析的“主流”。 (Kernberg,1993)。
分析的主流與互為主體客體關係取向的差別在於整合,當互為主體取向大都拒絕(或者不強調)驅力理論時,分析主流則對Fairbairn整合驅力與客體關係的理論運用有加。
法國分析學派也影響了這種在普遍概念上和解的最新發展趨勢。它們包括:聚焦於嶄新(或更新)的古老伊底帕斯情結;強調在嚴重的心理病理類型中,伊底帕斯與前伊底帕斯衝突的凝縮(condensation) ;並重新關注移情的情欲面向,多形倒錯的嬰兒性特質,還有它們在移情的反響。法國的影響還包括將發展的線性模式以交替(阿智:模式)加以取代,這種交替出現在(多個來源)衝突的同步凝縮,以及隨著時間產生的移情演變之間。並把這種交替視為伊底帕斯與前伊底帕斯關係辯證的一部分。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強調分析師的反思功能( reflective function),將其視為對病人自我反思的前提,這個考量為的是要把分析師的詮釋視為“第三位置”的反思,並將此三角(triangulation)引入移情/反移情糾結的共生本質中(Green,1986)。和拉康相呼應的是,這種觀點意味著聚焦於分析師的詮釋,以促進病人進入“象徵界”(“symbolic order),進入古老的伊底帕斯情結(Lacan,1966)。雖然法國精神分析的影響目前可能像是“風中的蘆葦”(阿智:原意稻草,但我將之譯為蘆葦,比喻影響不大且很脆弱) - 跟美國比起來,較為歐洲與拉丁美洲的分析圈所重視 - 但之前提到的普遍和解,對我來講似乎更會在北美建立。
在三大支流合併到分析主流的過程中,沒有發生轉變的地方是:以技術的中立(technical neutrality)作為精神分析架構的基本面。 它決定了移情被回應與被分析的方式,也是分析師詮釋概念化(interpretive formulations)的基本面向。(待續)
※阿智翻譯的文章是: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hird Position
※作者:Otto F. Kernberg, M.D.
http://www.pep-web.org/document.php?id=ajp.057.0297a&type=hitlist&num=1&query=zone1%2Cparagraphs%7Czone2%2Cparagraphs%7Ctitle%2CThe+Nature+of+Interpretation%3A+Intersubjectivity+and+the+Third+Position%7Cviewperiod%2Cweek%7Csort%2Cauthor%2Ca#hit1
※圖片選自網路
了解跨性別
最近常在媒體看到
跨性別朋友被霸凌的慘案
這些霸凌的等級直達謀殺
內心非常震撼悲傷
也認清性別平權不是喊喊口號的政治正確就好
而是一個細緻的心理過程。
教育就是這個過程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性別做為一種社會常規
做為人類感受自己,看待世界,
建立心理認同的方式,
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希望多元的性別教育,可以不要讓性別成為投射的陰影
而是讓性別成為豐富彼此生命的養份。
※ 跨性別繪本導讀: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389307954463715&id=100001535713155
關於同志孤單的種種
週末夜花時間把這篇報導最後部份完成,不覺已超過睡覺時間。
忽然想到此刻正是許多同志朋友玩樂釣人的時刻。
書房夜深人靜,不知會有那位同志朋友百無聊賴的時後,不經意看到這篇文章。
如果這篇報導可以安慰到寂寞的心情……
想到這裡,晚睡也值得了。
20170326,凌晨一點,阿智譯後
根據研究,當今同性戀比異性戀高出2到10倍的自殺率。高出兩倍的憂鬱症。正如過往的大流行,這些創傷似乎集中在男同志身上。
最近針對紐約市男同志的調查中,四分之三患有焦慮或憂鬱,藥物或酒精濫用,或有危險性行為,或者以上三者的組合。
儘管我們的“受訪家庭”都說,男同志比直人或女同志擁有較少的密友。一項針對愛滋病診所的護理師的調查中,一位受訪者告訴研究人員:“這不是他們不知道如何拯救生命的問題,而是他們是否知道自己的生命值得被拯救。"
我們在洞穴麵條吧共進午餐。 時值十一月,他身着牛仔褲、膠鞋和婚戒翩然降臨。“同志婚姻?”我說。 “一夫一妻制”他說。 “我想這些(阿智:行頭)讓我們持有進入這個城市的鑰匙。
當50,60年代差異首度出現時,醫生認為這是同性戀本身的症狀,只是當時被稱為“性反轉”(sexual inversion)的眾多表現之一。 然而隨著同性戀運動興起,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消失,這些差異的解釋轉向了創傷。 男同志被踢出自己的家,他們的愛情生活是非法的。 當然他們有驚人的自殺率與憂鬱。 “我也有類似的想法” Salway說,“同性戀自殺是過去時代的產物,或者集中在那些看不到出路的青少年身上。"
在他看了數據之後。了解到問題不只是自殺,不只是倍受折磨的青少年,也不只發生在恐同染指的地區。 他發現,無論在何處,哪個年齡層,男同志都有更高的心血管疾病,癌症,失禁,勃起障礙,過敏和哮喘 - 所有你能想到的疾病我們無一不得。Salway最後發現在加拿大有更多男同志死於自殺,而不是愛滋,這種情況持續多年。 (這也可能是美國的實況,他說,但沒有人覺得夠嚴重而去研究它。)
男同志正如Keuroghlian所言,“總是預期著被拒絕。”我們不斷地掃描社會處境,想著哪些是我們可能無法融入的部分。 我們掙扎於自我肯定,總是循環地上演著社交的挫敗。”
然而這些症狀最奇怪的是,大多數人的外表根本看不出來。自從看了數據,Salway便開始走訪那些企圖自殺然後存活下來的男同志。
“當你問他們為什麼要自殺? ”他說,“多數人都沒有提到任何關於同性戀的事。”相反的,他說,他們告訴他的是關係問題,職業問題, 金錢問題。 “他們並不覺得性特質是他們生活中最突出的面向。 然而,卻是一個更可能造成自殺的數量級(an order of magnitude)。
對於同志,由於我們少數族群的處境隱而未顯,效應因此被放大。 不僅我們必須做所有額外的工作,回答內部所有的問題,而且我們也無法跟朋友父母討論這些。
這也是我度過青春期的寫照:"如履薄冰,偶有失足,當壓力破表,再用盡全力修補。"就像有次在水上公園,我的中學同學在等待遊戲的片刻發現我盯著他瞧: “老兄,你剛在看我嗎?”他說。 我試著轉移話題,像是“對不起,你不是我的菜”之類的 。 然後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擔心他怎麼看我,但他沒有再提起。 所有的霸凌場景僅僅發生在我腦袋。
或者,正如Elder 所說,身處暗櫃裡就像有人在你手臂輕輕碰一下,一遍又一遍。 剛開始它很煩人。 過了一會,它令人抓狂。直到最後,它們僅變成腦袋中的一件事情,然後每天處理它的壓力開始在你身體積累。
一項2015年的研究發現,同志分泌較少的皮質醇(cortisol),這是一種壓力調節激素。 他們的系統在青春期如此激活,並且持續運作,因此在他們長大成人後反而變得遲鈍無感。偕同研究者 Katie McLaughlin說。 2014年,研究人員比較直男與同志青少年的心血管風險。 他們發現同志小孩並無更多的“壓力生活事件”(直人小孩也會面對的問題),但他們經歷的種種卻對他們的神經系統造成更多損害。
“我從不擔心我的家人會恐同,”他說。 “兒時我總習慣在身上裹一條毯子,感覺像洋裝,然後就在後院跳起舞來。 我的父母覺得這很萌,因此他們拍了視頻,拿給祖父母看。 當他們全部盯著視頻瞧,我則躲在沙發後,感到十分害臊...那一年我肯定有六七歲。
就這樣過了許多年,去年感恩節回家探望父母,因為壓力過大,導致無可遏抑地想做愛。當他終於找到一個住在附近的人願意約,立馬衝進父母房間翻箱倒櫃,看看是否有威爾鋼。
"不知是第三或第四次了! "他說。
Adam 現正參加12步驟性成癮治療計劃,已經六個禮拜沒有性生活了。 在此之前,他最久沒有性的時間僅有三四天。
你背負著孤獨長大,累積許多包袱,然後你來到卡斯楚、雀兒喜、還有男孩鎮,想著有朝一日可以因為原來的你被接受。然後你意識到這裏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包袱,突然間你不是因為同志本質被拒絕,而是因為你的體重、收入、還有種族。"昔日飽受霸凌的孩子" Paul說:"現在反過來霸凌自己人。"
"男子氣概的挑戰在男性群體容易被放大,"Pachankis說。"男子氣概是危險的,它經常必須付諸行動,或者防衛、或者囤積。研究顯示:在一群男人中如果你膽敢挑戰男子氣概,他們會氣燄高張,開始表現出財務冒險,或想揍人的樣子。"
近十年傳統同志場所-酒吧、夜店、與三溫暖-逐漸消失,被社群媒體取代。超過70%的男同志會使用Grindr 與 Scruff 來認識彼此。2000年,20%的同志伴侶就是透過社群媒體認識對方。2010年已經上升到70%。透過朋友介紹的同志伴侶從原本的30% 下降到12%。
我們告訴他:"恭喜!你的會員卡跟導覽手冊正在隔壁房等著你," Halkitis回憶道:"但他太緊張了,完全聽不懂我們的玩笑。"
James成長於皇后區,在一個充滿情感的自由派大家庭長大,與公開現身的同志小孩一起上公立學校,Halkitis說:"然而,仍有莫名的情感困擾,也就是在理性上知道一切沒事,但情感上仍讓自己躲在暗櫃。"
James的憂傷發生在2007,我的在1992,Halkitis說他的則在1977。因為驚訝於姪子與他共享同樣的經驗,因此決定下一本書要探討衣櫃裡的創傷。
"既使到現在,既使身在紐約,既使有接納的家長,現身仍然充滿挑戰,"Halkitis說:"或許永遠都是。"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件事?當我們把同志婚姻與反歧視法視為權益的保障,關於法律與健康的關係還有甚麼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當時14個州通過將婚姻定義為男女之事的憲法修正案。 這些州的男同志情緒障礙立馬增加37%,酒精成癮增加42%,廣泛性焦慮則增加了248%。
這些數據最令人心寒的是,生活在這些州的同志權益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在修正案通過前,我們沒有辦法在密西根結婚,在修正案通過後,我們依舊無法在密西根結婚。法律象徵主流群體知會同志他們不悅之事的方式。更糟的是,焦慮與憂鬱的攀升並非發生在憲法修正案的州,而是發生在全美的同志社群。法律的運作使我們受苦受難。
事實就是,我們國家最近選出了一個亮橙色的混世魔王(阿智:指川普),公開且急切地透過行政命令逆轉了同志社群過去20年來的努力。並且傳達給同志(特別是年輕且需緊抓住認同的小同志)赫然入目的恐怖訊息。
反霸凌研究機構GLSEN的主席Emily Greytak告訴我,從2005到2015,因性取向被霸凌的青少年比率完全沒有下降。美國只有30%的學區擁有特別針對LGBTQ兒童的反霸凌政策,其他無以數計的學區則在政策上阻止教師以正向的方式討論同性戀。
這些限制使得孩子在面對少數族群壓力時倍感艱辛,幸好不是每位老師以及曲棍球校隊都要接待同志在家過夜 (阿智:作者以反諷的修辭,鋪陳出同志最害怕的社交情境)。
Marquette大學的研究員Nicholas Heck最近四年籌辦了中學同志的支持團體。帶領他們與同學,老師,雙親互動。幫他們將性別特質所產生的壓力,從琳瑯滿目的青春期壓力中區分開來。
舉個例子,一位少年正面臨父母希望他念藝術而非財經的壓力,雖然父母立意良善-希望未來不要進入恐同者橫行的科系-但重點是他已經夠焦慮了:假使他放棄財經,是否就意味著他向汙名屈服? 假使他聽從父母修習藝術卻仍被霸凌,還會告訴父母他的痛苦嗎?
Heck說:訣竅是讓孩子可以公開討論這些問題,因為少數族群壓力最顯著的標誌就是閃躲。
譬如孩子在大廳撞見貶抑的批評時,常會刻意從另一側樓梯下樓,或者塞上耳機充耳不聞。當他們尋求老師協助卻得到不置可否的回應時,往往會讓他們停止向大人尋求僻護。
Heck說:研究中的孩子開始拒絕為這些霸凌負責,他們學到雖然無法改變環境,至少要停止責備自己。(阿智:最常見的說法是這個孩子特立獨行過於囂張,因此被討厭,希望孩子可以改變個性與性特質好適應環境。)
Salway告訴我:"我甚至不知道你要往哪裡去。" 問題在於我們對心理疾病、愛滋防治、與藥物濫用建立了不同的立論,然而所有的結果都顯示出:這些不僅是三種流行病而已,而是一種。
被拒絕的人傾向於自我治療,使其可能發生危險性行為,進而感染HIV,然後這些結果又迫使他們被拒絕,如此下去沒完沒了。
過去五年,隨著這種彼此相關的證據逐漸積累,許多心理學家和流行病學家開始把同志的疏離(alienation)視為一種“症候群”:一大群健康相關的問題,沒有一個可以單獨修復。
歷經多年的情感閃避後,"許多男同志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感受,"他說。當他們的伴侶說:"我愛你"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回答:"我愛煎餅。"他們會與尋尋覓覓的那人分手,竟是因為那人把自己的牙刷留在他家。又如同我所認識的大多數人,與陌生人做愛時沒有自我保護,竟是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如何傾聽自己的恐懼。
只消指出這種模式便可以得到巨大的進展:Pachankis的病人短短三個月便減輕了焦慮與憂鬱,藥物使用,還有無套性行為。他正打算將此研究擴展到更多城市,更多受試者,以及更長的試驗期。
依然有更多的異性戀小孩遠遠超過同志小孩,我們仍會被他們孤立。在某些層面上,我們仍會在家庭、學校、與鄉鎮中孤單地長大。但這或許不是壞事,跟主流保持距離可以轉化成內在的某些東西:我們的風趣、我們的彈性、我們的同理心,我們打扮與唱跳的本領,都是我們的內在資源。我們必須認知到爭取更好法律與環境的重要-就像我們努力彼此善待。